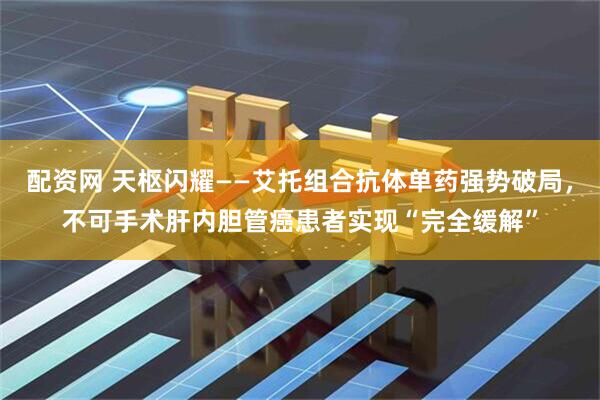那天是1950年1月初,成都寒意正浓。 西南军区司令部里,一场常规的接待工作正在进行。 贺龙坐镇,准备迎接刚刚起义的国民党军官代表。 气氛紧张又克制,毕竟刚投诚,彼此还带着些试探。 就在这时候,站在贺龙身边的一位年轻下属突然来了句:“他长得真像我哥。”说完自己都愣住了,空气一下凝固了几秒。 对面的联络官也听见了恒利决策,条件反射似的盯过来,眼神闪了一下,然后脱口而出:“马千木?”
那位下属激动得眼圈都红了,几步上前抓住对方的手:“哥,是你?” 这一刻,周围人都还没反应过来,两个曾在战火中各奔东西的兄弟,就这么在司令部里重逢了。 谁也没想到,分别二十多年,竟然会在这样一个场合再见。 这是马识途和马士弘的故事。 一个是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老战士,一个是国民党起义将领。 他们的相遇,像个意外,其实是时代的缩影。
展开剩余80%说起来,这家人原本是在重庆石宝寨的一个书香门第。 父亲马玉之当过三任县长,对孩子的教育特别看重。 马士弘是家中三子,马识途是第五个。 小时候,兄弟几个都按家规恒利决策,五岁习字,六岁进私塾。 但这个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:儿子年满十六就得独自闯荡,不许靠家里。1931年,16岁的马识途考上了北平大学附中,独自坐船北上。 那年,他三哥马士弘已经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了。
本来是个兄弟团聚的机会。 可天不随人愿,”九一八”事变爆发。 日军入侵东北,北平一夜之间陷入战时状态。 马识途刚到北平,就看见伪警当街用警棍打女学生,血流满地。 他吓坏了,跟着一群东北学生蜷在操场角落里偷偷哭。 那时候,他还想着靠读书、搞工业来救国。
可没多久,现实给了他一记重锤。 1933年,他挤着火车去上海,连车厢都挤不进去恒利决策,只能爬到车顶。 火车转弯时晃得厉害,他藏在襟口的一支钢笔“咕噜噜”滚了出去。 他急着去抓,被人一把摁住:“这是车顶,你不要命啦!”钢笔就这么掉了。 那一刻,他心里的“工业救国梦”也掉了。 他意识到,这个国家连个能安心念书的地方都没有。
于是,他转了方向,投身抗日运动。 而此时的马士弘,早已脱下学生装,穿上军服。1934年,他考入黄埔军校第11期。 毕业后被派往蒋介石直接管辖的“新生活运动”执行机构,还被授予“中正剑”。 在南京工作时,他刚好碰上弟弟被捕的消息,亲自出面把马识途从监狱里捞了出来。 两人一见面,没说几句,又匆匆分别。 一个去了南京继续读书,一个回部队报到。
那是1936年。 谁也没想到,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。 抗战全面爆发后,马士弘转入前线,跟随罗广文部队作战。 他在小溪口指挥突击队炸毁日军油库,火苗引燃江边炮艇,趁乱收复谭家铺。 后来又在常德会战中头部负伤,硬是拒绝撤退,坚持到最后。 马识途这边,早已成为中共鄂西特委交通站的重要成员。
他和妻子刘蕙馨共同执行隐蔽任务,后来刘蕙馨被叛徒出卖,入狱后坚守党的机密,最终牺牲。 她被捕那天其实是有机会逃的。 邻居家被误抓走,敌人还没发现她。 她完全可以趁机转移。 但她没走。 因为家里还有党的文件。
她选了留下。 等文件都烧完,敌人破门而入。 在狱中,她咬牙撑过酷刑。 马士弘得知消息后想办法营救,她却大声劝他:“三哥,你婆婆妈妈地干嘛!快点动手!”最终,刘蕙馨牺牲在敌人的牢房里,年仅二十七岁。 马识途一边继续组织工作,一边拼命找女儿的下落。 他们的孩子,在那年冬天也不见了。
战后,局势再度紧张。 国共开始内战。 马士弘几次想脱下军装,被上级拒绝。 他越来越看不惯蒋介石的做法。 尤其是听说弟弟差点死在特务手里之后,心里更不是滋味。 1949年底,四川战局已定。 罗广文率部起义,马士弘作为联络官,代表起义军前往成都报到。 没想到,走进司令部的那一刻,他看见了那个站在贺龙身旁、穿着我军军装的中年人。 那是他失散已久的五弟。 二十多年,兄弟俩从未联系。 各自走了一条看似完全不同的路,却在这个节点上重逢——不仅是命运的安排,更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写照。 战后,马士弘被安排在新中国的军政系统工作。 马识途则成了著名作家,为国家文化事业出力多年。 他写过一本《我行我素幸识途》,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,也是在说:庆幸自己没走错路。 晚年,马士弘曾在一次采访中讲起那次重逢。 他说:“那天,我一进门,就觉得他眼熟。 可我不敢认。 是他先开口的。” 从那以后,再也没人这样叫过他“马千木”。 参考资料: 马识途,《我行我素》,作家出版社,2003年。 马识途口述,谭楷整理,《马识途口述历史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5年。 罗广文,《抗战中的西南战事》恒利决策,中国文史出版社,1991年。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,《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(1949-1978)》,中共党史出版社,2011年。
发布于:天津市翔云优配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